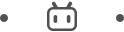2015年,村上的出道作《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首次在英语圈出版,与中文的村上作品出版不同,英译本的《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是合并成一本出版的,即《风/弹子球》(WIND/PINBALL)。
这一序言和《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施小炜译,新经典)的第二章‘刚当上小说家那会儿’内容有一定的重合,但一些细节和顺序是有变动的,润色的过程中有参考其内容。这本《小说家》我是很推荐阅读的,即使你不看村上的作品,也会受益良多。(如果你没看过这本书,那就更好了,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序言)
关于我的餐桌小说的诞生
两部短小说的介绍
大多数人,我指的是大部分身处日本社会的我们——从学校毕业,再到找工作,然后过段时间就结婚。甚至我一开始也打算遵循这一模式。或者说,至少那是我曾经想象过会成为现实的事情。然而事实是我结婚了就开始工作,再(不知为何)终于设法毕了业。换句话说,我选择的人生顺序与常规截然不同。
从我浮现出讨厌在公司上班的想法起,我决定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一个可以听爵士乐唱片、提供咖啡、小吃和酒精的地方。简单,相当乐观的想法,经营一家这样的店,我想,可以让我从早到晚听我喜爱的音乐。可问题是,我和妻子还在学校时就结婚了,我们没有钱。因此,头三年我们像奴隶一样同时打好几份工,尽可能地存钱 。之后我问了一圈,从朋友那不管是多少钱都借过来和省下家庭开销。我们把凑到的钱,在东京西郊常有学生聚集的国分寺开了一家咖啡小店/酒吧,那时是1974年。
那时开家自己的店远比现在花费少得多。周边有和我们一样,不惜一切代价决定逃避“上班人生”的年轻人开着小店。咖啡厅、餐厅、杂货店和书店——你有命名权。许多相邻的场所都被我们这一代人拥有和经营。国分寺保留着强烈的反主流的氛围,大量从不断衰退的学生运动中退学的人在这一带经常出没。 在那个年代的世界各地,个人仍然能在体制内找到空隙。
我从父母家里搬来了以前用过的立式钢琴,开始在周末的店里提供现场音乐。国分寺生活着很多年轻的爵士乐手,他们乐于(我认为)为我们支付的微薄金额演奏。很多后来成了知名的音乐人,即使是现在,我有时在东京的爵士乐俱乐部还能偶遇他们。
尽管是做着我们喜欢的事情,偿还债务仍是一个长期的挣扎。不单欠银行,还欠支持我们的人。有一次,我们为银行的每月还款发愁,深夜,我妻子和我耷拉着脑袋,疲惫地走在街道上,无意间发现了地上有一些钱。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共时性原理,还是某种神圣的指引,但那笔钱刚好是我们需要的金额。因为还款截止到明天,真的是在最后一分钟得救了。(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人生节点发生过好多次。)大部分日本人可能会做正确的事,把钱上交给警察,但我们撑到了极限,无法靠着这样的善意存活下去。不过,毫无疑问,这很有趣。我年轻,正值盛年,可以整天听我喜爱的音乐,还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不需要挤上塞满人的通勤电车,也不用参加恼人的会议,更不必奉承我不喜欢的领导。我(反而)有机会见各种有意思的人。
就这样,我的二十岁月花费在了偿还贷款和从早到晚地做艰苦的体力活(做三明治和鸡尾酒,赶走满嘴脏话的顾客)。过了几年,我们的房东打算翻修在国分寺的建筑,所以我们搬到了更新潮和更宽敞的千驮谷,靠近东京的市中心。我们新的场所有足够的空间放下三角大钢琴,不过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我们的债务又增加了。所以,我们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善。
回望过去,我只记得我们如何幸苦地工作。我想,大部分人的二十岁月都相对自在得多吧,但我们实在没有时间享受无忧无虑的年轻时光,仅仅勉强过得去。只要我一有时间,我都拿来看书。读书和音乐是我最大的乐趣。不管我有多忙,多没钱,多精疲力尽,没有人能从我手上夺走这些快乐。
随着我的二十岁月的尾声接近,千驮谷的爵士乐小店终于开始显露出稳定的迹象。当然,我们没法放轻松——我们还欠着钱,而且我们的生意起起落落,但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一九七八年四月的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到神宫球场看棒球比赛,球场离我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不远。是那一年的中央联盟的揭幕战,开球仪式在下午一点(First pitch),由养乐多燕子队对决广岛鲤鱼队。我那时已经是养乐多燕子队的粉丝了,时不时会顺道去看场比赛——作为散步的替代品。
当时的燕子队是一只常年垫底的弱队(你大概能从它的名字猜到),运营的资金有限,就没有知名度高的大牌球员,他们想当然不会很受欢迎。虽然是赛季揭幕战,但只有寥寥几个球迷坐在外场席。我躺在草坪上边喝啤酒边看球赛。那时候这里还没有廉价座位,只有一面长满草的斜坡。
天空一幅熠熠生辉,湛蓝的样子,散装的啤酒(生啤酒)冻得冰凉,白色的球在绿色的草地上格外显眼,这是我很久以来,看的第一场现场球赛。燕子队的头阵击球手是戴夫·希尔顿(Dave Hilton),是刚从美国来的一名清瘦的无名小辈。他排在击球顺序的第一位。第四位击球队员叫查理·曼纽尔(Charlie Manuel), 他后来因为在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和费城人队当总教练而出名。不过当时的他是一个真正的猛男,一个被日本球迷称为“红魔”的强击手。
我记得广岛队那天的首发投手是外木場義郎(Yoshiro Sotokoba),养乐多队则以安田猛反击(Takeshi Yasuda)。第一局的下半场,希尔顿击中了義郎投出的第一球,球进到了左外场形成了二垒打。球棍击中球发出的称人心意的清脆声回响在整个神宫球场,疏疏落落的掌声在四周响起。在那一刻,我突然被毫无理由、毫无根据的念头击中了:我想,我是能写小说的。
我依然能准确地回想起当时的感受。那就像有什么东西从天上飘落,然后我干净利落地用手接住了它,我不清楚它为什么会落到我手中。我那时就不太明白,直到现在也是。无论是何种原因,它确实发生了。它像是一种天启,或者说“epiphany”会更合适的。我可以确定的是我的人生从那一刻发生了急剧且持续的变化——在戴夫·希尔顿在神宫球场挥出那一击精彩响亮的二垒打时。
比赛结束后(养乐多赢了,我记得),我搭乘电车去新宿买了一捆稿纸和一支钢笔(a fountain pen)。文字处理机和电脑在那个时候还没出现,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手写所有内容,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作的感觉非常新颖,我记得当时的我是多么得激动。我已经很久没拿起笔在纸上写东西了。
从那之后的每个结束工作的深夜,回家的我都会坐在厨房的餐桌上写小说。黎明前的几个小时是我仅有的自由时间。差不多六个月之后,我写了《且听风吟》。我在棒球赛季结束时完成了初稿。顺带一提,那一年的养乐多燕子队竭力克服不利条件,打破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测,赢得了中央联盟的冠军,接着又在日本系列赛击败了太平洋联盟冠军(the Pacific League champions),和有投手阵容深度的阪急勇士队(Hankyu Braves)。这真是一个奇迹般的赛季,让所有养乐多队的球迷情绪一路高涨。
《且听风吟》是一部篇幅较短的小说,比起长篇小说更接近于中篇小说。可写它也花了好几个月和不少努力。当然,有部分原因是我不得不利用工作之后的有限时间,但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我对如何写一部小说没有头绪。实话说,我爱读的都是19世纪的俄罗斯小说和美国硬汉侦探小说,但我并没有认真翻看过同时代的日本小说,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流行什么样的日语小说,也可以说我不知道该如何用日语写小说。
几个月来,我纯粹靠着猜测写作,采用看似可行的风格然后坚持了下来。不过阅读成果时,没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我的书看似符合小说的要求,它也有点无聊了,整体而言缺乏热情。我不免低落地想:如果作者都这样觉得,读者的反应可能会更不好。 似乎只是因为我没有它需要的东西。 在正常情况下,它会在那里终结——我会一走了之。 但在神宫球场的草坡上得到的顿悟,却依然清晰的刻在我的脑海里。
回想起来,我无法写出一部好小说是很自然的。 试想一下,一个像我这样从来没写过什么的人,突然能产出一些出色的作品。我所尝试的事情是不可能做成的。于是我对自己说,别再试着写复杂的东西了。忘掉一切关于“小说”和“文学”的预设吧,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自由地书写你的情感和想法。
畅快地表达一个人的想法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做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 对于我这样的纯新人来说,这尤其困难。 为了重新开始,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摆脱我的一摞手稿纸和我的钢笔。 只要它们摆在我面前,我所写的东西就感觉像“文学”。 我从壁橱里拿出我的旧 Olivetti 打字机替换掉它们。 然后,我就决定做一次实验——用英文写小说的开头。 既然我愿意尝试任何事情,我想,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不用说,我的英语写作能力并不强。 我的词汇量非常有限,对英语语法的掌握也一样。 我只能写简单的短句子。 也就是说,无论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想法多么复杂和丰富,当它们来临时,我甚至不能试着把它们转换出来。 语言必须简单,用易于理解的方式表达我自己,删去不必要的赘述,使(小说)形式紧凑,一切都安排在一个大小有限的容器中。 所诞生的是一种粗糙的、未耕耘的散文体。 然而,当我努力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时,一种独特的节奏开始形成。
由于我是在日本出生和成大的,日语的词汇和思维方式已经填满了我的语言系统,就像一个挤满牲口的畜棚。当我试图用日语表达我的想法和感受时,那些家畜就开始四处乱窜,语言系统随之崩溃了。反而用外语写作时,我受限于种种限制,这个障碍消失了。这也让我发现:是可以用有限的词汇和语法结构来表达我的想法和感受的,只要我将它们有效地进行配搭,并以一种独特的风格巧妙地将它们联系在一起。最终,我认识到,不需要用很多艰深的词汇,也不必试图用优美的句子来打动人们。
很久以后,我发现作家阿戈塔·克里斯托夫(Agota Kristof)写了许多精彩的小说,和我风格非常相似。克里斯托夫是一名匈牙利公民,1956 年她在她的祖国动荡期间逃到瑞士纳沙泰尔(Neuchâtel)。她在那里学过——或者说被迫学过正宗的法语。然而,正是通过用这样的外语写作,她成功地开拓出一种新颖独特的风格。风格的特点是基于强有力的短句节奏,措辞从不迂回,但常常显得直率,以及描述扼要且没有情感包袱。她的小说被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暗示着隐藏在表面之下的重要事物。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她的作品时,觉得有莫名的熟悉感。挺巧的是,她的第一部小说《笔记本》(The Notebook)于 1986 年问世,与《且听风吟》相隔仅七年(1979年)。
我发现用外语写作所带来的奇特效果,从而掌握了一种我独有的创作节奏,我将 Olivetti 放回壁橱,再次拿出那一叠稿纸和钢笔。然后我坐下来,将我用英语写的一个章“翻译”成日语。好吧,用“移植”可能更准确,因为它不是直接逐字翻译。在这个过程中,毫不意外地诞生了一种新的日语风格。这将是我的写作风格——我所开拓的。我现在想明白了,这就是我该掌握的方式。当我不再被语言蒙蔽时,那一刻我的视野开阔了。(the scales fall from someone’s eyes)
有人说,你的作品读起来有译作的感觉。我不是很能理解这句话的确切含义,但我觉得它只切中了一点,另外的东西则完全忽视了。由于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Novella)的开头段落是字面意义上的“翻译”,因此这一评论不全是错的。可它只适用于我的写作过程。我首先用英语写作再“翻译”成日语所寻求的,不亚于创造一种朴素的“中性”风格,让我可以更自由地表达。我对创作一种淡化的日语形式不感兴趣。为了能够不做作地表达自我,我想使用的是一种尽可能剥离了所谓“文学语言”的日语。这需要采取决绝的方式。说得极端点,当时我不过是把日语当成一种实用的工具而已。
我的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是对我们民族语言的严重冒犯。然而,语言是一种非常顽强的东西,一种基于长久历史的顽强。无论怎样对它,它的自主权都不会丢失或遭到严重损坏,即使这种处理相当粗暴。所有作家与生俱来的权利就是他们能用想象到的每一种手段来试验语言的可能性——没有这种冒险精神,就不可能有新的东西诞生。我的日语风格与谷崎(润一郎)不同,也与川端(康成)不同。这是很正常的。毕竟,我是另一类人,一个叫村上春树的独立作家罢了。
春天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晨,我接到文学杂志《群像》的一位编辑的电话,告诉我《且听风吟》已入围他们的新人奖。从神谷体育场的赛季揭幕战到现在快一年了,我也三十岁了。已经是上午 11 点左右,我仍然睡得很死,因为前一天晚上工作得很晚。我迷迷糊糊地拿起听筒,但一开始我不知道电话那头的是谁,也搞不清他在说什么。实话说,那个时候我压根不记得把《且听风吟》投给了《群像》这一回事了。一旦我完成了手稿并把它交到别人手上,我的写作欲望就完全消退了。可以说,创作它是一种反抗行为——我很容易就能写出来,就像我想到的一样——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它可能会进入候选名单。实际上,我已经把我仅有的原稿寄给了他们。如果他们没有选择它,它或许就没了。 (《群像》 不会退回被拒绝的手稿。)我也很可能不会再写下一部小说了。人生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编辑告诉我,五个人入围,包括我在内。我很惊讶,可那时我困得很,所以我没怎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起床,洗漱,穿好衣服,然后我和妻子出去散步。就在我们路过当地的小学时,我注意到一只旅鸽躲在灌木丛里。把它捡起来时,我看到它似乎断了一只翅膀。一块金属碎片附着在它的腿上。我将它轻轻地捧在手心,带到最近的青山表参道(Aoyamaomotesando)的警察局。当我沿着原宿(Harajuku)的街道走到那里时,受伤的鸽子的温暖落入我的手中。我感到它在颤抖。那个星期天阳光明媚,那些树木、建筑物和商店橱窗都在春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十分好看。
就在那时它击中了我。我将要赢得新人奖,进而成为一名小有成就的小说家。这是一个厚颜无耻的预测,但在那一刻我完全确信它会成为事实,不是从逻辑上推测,而是直觉上就认为如此。
第二年我写了作为《且听风吟》的续集《1973年的弹子球》。那时我还在经营着爵士乐小店,也就是说《弹子球》依旧是在深夜的餐桌上写的。 我把这两部小说称呼为餐桌小说,是出于我那夹杂着些许羞愧的爱意。完成《1973年的弹子球》后,我萌生出了成为全职作家的念头,就把店铺转让了。我很快就着手我的第一部标准长度的小说——《寻羊冒险记》,我认为这是我作为职业小说家的真正起点。
无论如何,这两部篇幅稍短的小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是完全不可替代的,就好像是很久前的朋友。似乎和它们再无相见的可能,但我不会忘记与它们的友情。它们在我过往的岁月是至关重要且珍贵的。它们温暖过我的内心,用我的方式激励了我自己。
我依然能很清晰地记得,我在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天,在神宫球场的外场席的草坪上,有什么东西飘落在我手上的感触。以及一年后,那个春天的下午,在千驮谷小学附近,同一双手捡起那只受伤的鸽子所感受的温暖。每当我在思考写小说意义着什么时,我总是会唤起那些感触。这样的触觉记忆教会我去相信我所拥有的(天赋),并梦想它所提供的可能。直到现在,这些感触仍然存留在我心中,真是太好了。
2014.06


「艾尔登法环」梅琳娜手办开订 立体手办▪

万代「艾尔登法环」白狼战鬼手办开订 立体手办▪

「夏目友人帐」猫咪老师粘土人开订 立体手办▪

「五等分的新娘∬」中野三玖·白无垢版手办开订 立体手办▪

「海贼王」乌索普Q版手办开订 立体手办▪

良笑社「初音未来」新手办开订 立体手办▪

「黑岩射手DAWN FALL」死亡主宰手办开订 立体手办▪

「盾之勇者成名录」菲洛手办登场 立体手办▪

「魔法少女小圆」美树沙耶香手办开订 立体手办▪

「咒术回战」七海建人粘土人登场 立体手办▪

「五等分的新娘」中野二乃白无垢手办开订 立体手办▪

「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芸芸粘土人开订 立体手办▪

「公主连结 与你重逢」六星可可萝手办开订 立体手办▪


「女神异闻录5」Joker雨宫莲手办开订 立体手办▪

「间谍过家家」约尔・福杰粘土人登场 立体手办▪


「街角魔族 2丁目」吉田优子手办开订 立体手办▪

「火影忍者 疾风传」旗木卡卡西·暗部版粘土人登场 立体手办▪

「佐佐木与宫野」宫野由美粘土人开订 立体手办▪

「盾之勇者成名录」第2季拉芙塔莉雅手办开订 立体手办▪

「咒术回战」两面宿傩Q版坐姿手办开订 立体手办▪

「DATE·A·BULLET」时崎狂三手办开订 立体手办▪

「狂赌之渊××」早乙女芽亚里粘土人开订 立体手办▪

「魔道祖师」魏无羨粘土人开订 立体手办▪

「新·奥特曼」奥特曼手办现已开订 立体手办▪